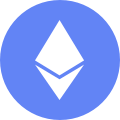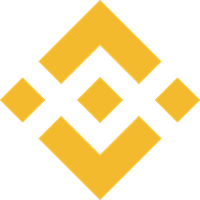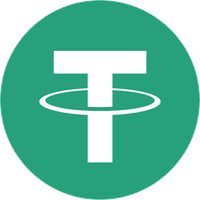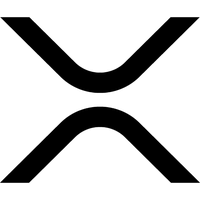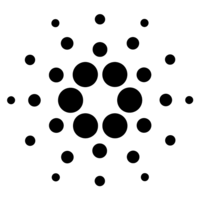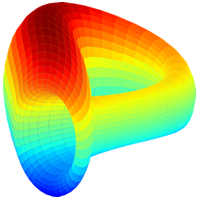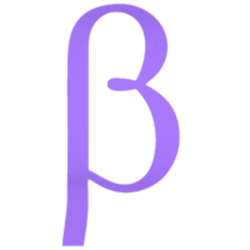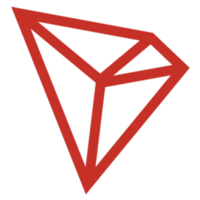区块链结构呈现的制度意义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当我们将区块链技术实体当作是一种源自于我们自身理性表达的自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区块链系统认知为对“自然法权”的建构性还原。[1]在此,我们认知的区块链结构不仅仅是一种计算机语言的技术架构,也不仅仅是对分布式的信息低成本无阻隔传输的创新架构,更在于它的区块节点的自我定义能力和由此带来的被链接起来所有结构元素的重新定义。
区块链研究领域著名学者韩锋先生在他的《熵、区块链和人工智能》[2]一文中提到了顾学雍教授的“自治的语言系统”的概念,从纯科学范畴切入区块链系统直接揭示了区块链技术的“非技术性”。在此,这不仅仅为区块链研究和思考提供了一种方法,更是为区块链系统的性质给定了一种范式标准,自治的和自存在的。
从区块链技术层面上看,它的创新架构和自我定义能力,源自于分布式结构对中心服务器的摆脱、通过区块节点固化的链接关系使得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不可逆,从而达成数据的“自我证明”。这里须注意到的是,第一,区块链的时间维度(时间戳)确定了其“自我证明”的技术基础和理论基础。时间标准链接块链的有效性和同一性;第二,区块的公平性建立在分布式网络计算的随机性和分布式论证的确定性架构中,这即是通常人们推崇的区块链形成的技术属性不依赖任何个体或机构的任何方式的主导或主导意图,而是由分布式的任意“参与者”随机共生所致,这应该即是区块链“共治结构”的技术属性。
区块链系统的共识和共治结构
我们已经广泛地注意和认知区块链在某些制度建构意义上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可能就是区块链信任机制的价值,“通过信用共识,区块链不仅真正能够实现了全球货币、支付的全部功能······(还将)远远超出货币、支付和金融这些经济领域,将迅速利用其优势开始重塑人类社会的每个方面。”[3]区块链技术呈现的这一特质或者优势,及其由这个特质展现的未来预期,都应源自这一“信用共识”背后的基础价值共识。
社会发展进程和实践经验清楚地表明,一个社会治理结构及其制度表现,都由现实的法治形态和法治理念来支撑,这个支撑意味着法治理念作为社会治理结构和制度形式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又支持和保障它运行的连续和一致性,从而达到由一个共识结构支持的“共治结构”的形态。因此,揭示区块链系统基础价值共识,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为了应用指向,而是区块链系统固有性质的意识属性的理性表达,这是最终达成区块链应用和在其“共治结构”下完成社会法治结构升级的前提。
目前,对区块链的共识结构的讨论已经展开,笔者在《区块链、去中心化和自然法权》一文中初步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见解,那就是区块链的基础共识必须也一定是自然法权。我们通过对区块链的技术属性指出了它的自存在性,并揭示了其区块及其系统元素的同质性和无中心化,从它的无差别主体的自由性,确认了区块链元素的自然法权“标准”。
费希特在他的《自然法权基础》一书中,阐述的自然法权概念,最早地全面突破了神权论架构和康德的以道德理性为基础的权利关系架构,将自然法权建构在人性基础上,也就是说,自然法权首先是人的权利,它不来自神,而只是人的理性在人和人群之间的自然建构,既不可剥夺,也不被授予;第二,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建立在人的理性和经验之上,同时,它摒除了绝对理性的概念(它太像神了),承认和确定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从而为现实社会的法权关系和法治结构建立了包含经验基础在内的共识基础。这实际上为纯粹理性哲学走向实践的法哲学打开了通畅的思想通道。现代经济学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以有限理性为前提和分析参数的实践理论;第三,基于自然法权的社会组成,通过社会契约构建起现代制度体系(国家和法律)。契约结构和契约关系既是方法、形式,也是实践框架。在此,我们既能确定自然法权发生作用的方法和形式,也能延展自然法权实践中的内容。
显然,费希特的自然法权思想,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共识结构演变为共治结构的逻辑体系,是一个依理建构的思想过程和实践结构。同样,我们现在讨论和实践的区块链系统,也是一个应由自然法权为基础的、由共识结构走向共治结构的社会治理体系及其实践过程。与费希特的十七十八世纪、社会思想立足于破除神权走向现代性的年代不同,现代社会推崇的价值观念和人文思想早已成熟,尽管陈年旧思想仍会不断泛起沉渣,但现代性主流深深扎根于历史和现实而难以撼动。问题是自文艺复兴时期思想革命和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尽管东西方制度建构有着很大差异,但都存在“习惯性”地依照“绝对理性”基础建立实践体系和制度体系的问题,无论怎么解释他们的“绝对理性”,都在形态化的或者固化的“绝对理性”范畴中陷入矛盾,最终人的有限理性的“局限性”,导致社会实践的结果都不同程度远离他们的“绝对理性”,这在东方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表现更为明显,有限理性始终没有在其实践中建立起系统的行动标准。
区块链自然法权既是共识形态又是共治形态
那么区块链结构中呈现的自然法权形态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能否在此基础层面上达成自然法权的共识,并据此形成共治共同体?
第一,我们讲的自然法权概念不是只存在于区块链系统中的特殊概念,它一定是普适的和与社会存在相适应的。在我们这里的语境中,它必是基于理性的普遍意识。在这个层面我们无需做过多的解释,一如区块链本身不仅作为技术现象、更作为社会现象所基于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意识环境的理性前提。
第二,区块链系统不能预先假设有一个游离其之外的“设立者”,而只能有实践中的发起者。费希特指出,“理性的本质特征在于,行动者和受动者是同一种东西”。[4]区块链结构的技术理性是一个无中心化结构的自在体,当然也不能接受一个额外的“神在体”。即便是针对性应用的私链,其被设定也在于设定者的自我选择,用费希特的话来说,它要么是必然的,要么是自由的,不能设想设计者自我之外还有一个客体化的自我[5]。因此,反过来即可印证在“理性即行动”的推论下的区块及其链的理性一体、主客体一体。用通俗的话来说,大致可表达为区块链系统没有“上帝”,这也是区块链系统无中心化的实质和自然法权形态的基础。
第三,在区块链系统中,自然法权概念不是被引入的,它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不是由任何人给区块链系统填入了一个关于自然法权的共识,然后再在区块链当中演绎这个自然法权。任何区块链元素、主体或者参与者、发起者,都设定自己为理性的,理性即自由,进而它也必然设定他者为自由,一如设定自己为自由;在区块链基础设定中,“未加分割的行动”不仅是设定,还确定了自由共享的范围和方式,设定的自由不能全归于己,因为有他者的自由,自我和他者的有限自由在区块链一体实现全然的自由。“(自然)法权概念是关于自由存在者彼此的必然关系的概念”[6]在此,费希特已经论证了自由理性的存在体的必然结果就是自然法权。当我们从上述引证和对区块链确定性的认知中确认,区块链系统存在的技术特征必须以技术理性和参与主体的理性设定为前提,我们即可确认其自然法权的共识基础。
第四,我们已经否认了区块链系统游离其外的“设定者”,但它以理性存在者的自我设定为依据,本质上以设定自我为客体,“理性存在者对其自身的反思最终和最高的基质B必然是回归到自身的、自我规定的能动性”。[7]且基于上述理性存在者自由设定的同质性,自我设定的客体化同一于每一个他者的客体化,这样,任何设定者在区块链系统中不在是游离于外的设定者,在理性客体的区块链当中自我设定也客体于实践过程的同一的自然法权形式。
第五,区块链系统之所以有效,是由于基于其独特的技术特质和规定性,所达成的相关主体关系的确定性和效用性。其中最直接的内容便是它的契约设定,整个区块链系统就是某种契约关系的设定,其智能合约的发展前景是最初始的契约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技术延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逻辑上,这种契约关系的基石即所依据的基础共识必须被一劳永逸地写进区块链代码当中,哪怕只是基于共识的具体的契约约定。我们已经知道,区块链特质不可能容忍不确定的非理性条件,即便在存在诸多分歧的意见选择中,也必须确立系统主体之间最大公约数,一种不可剥夺、也不被授予的理性存在,这便是自然法权。这个最大公约数本质上是区块链参与者及所有主体,将区块链系统的效用性融合到了自由的界限内,“仿佛在他们之间划分了这个作为他们的自由范围的世界······所有的人都必须把不干扰那些与自己处于相互作用中的人们的自由确立为自己的法律。”“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法权概念的全部客体,即各国自由存在者之间的共同体。”[8]根据我们现有的对区块链系统的理解,这个共同体多针对了某种或某些现实的实践目标,并且具备在技术理性框架下的一致意见,实际上这是对内置权利认可的共识,最终是对法权基础的一致认同。如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有法权基础和具体信任目标的共治结构,一个有具体实践内容的和权利主体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共治结构既然以自然法权为内置共识,无论遵循什么样的实践原则和按照什么样的实践路径,最终必然会与现实的普遍的法权体系和法治结构向衔接。
作者:沙钱
责编:萌大大
稿源:资讯(http://www.8btc.com/natural-right)
- 参见:沙钱《区块链、去中心化和自然法权》http://www.8btc.com/blockchain-natural-right↵
- 原文见http://www.weiyangx.com/149996.html↵
- 龚鸣《区块链新经济蓝图及导读》第三章导读,新星出版社2016版第85页↵
-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一版,导论第1页↵
- 同上第9页↵
- 同上第3-4页↵
- 同上第6页↵
- 同上第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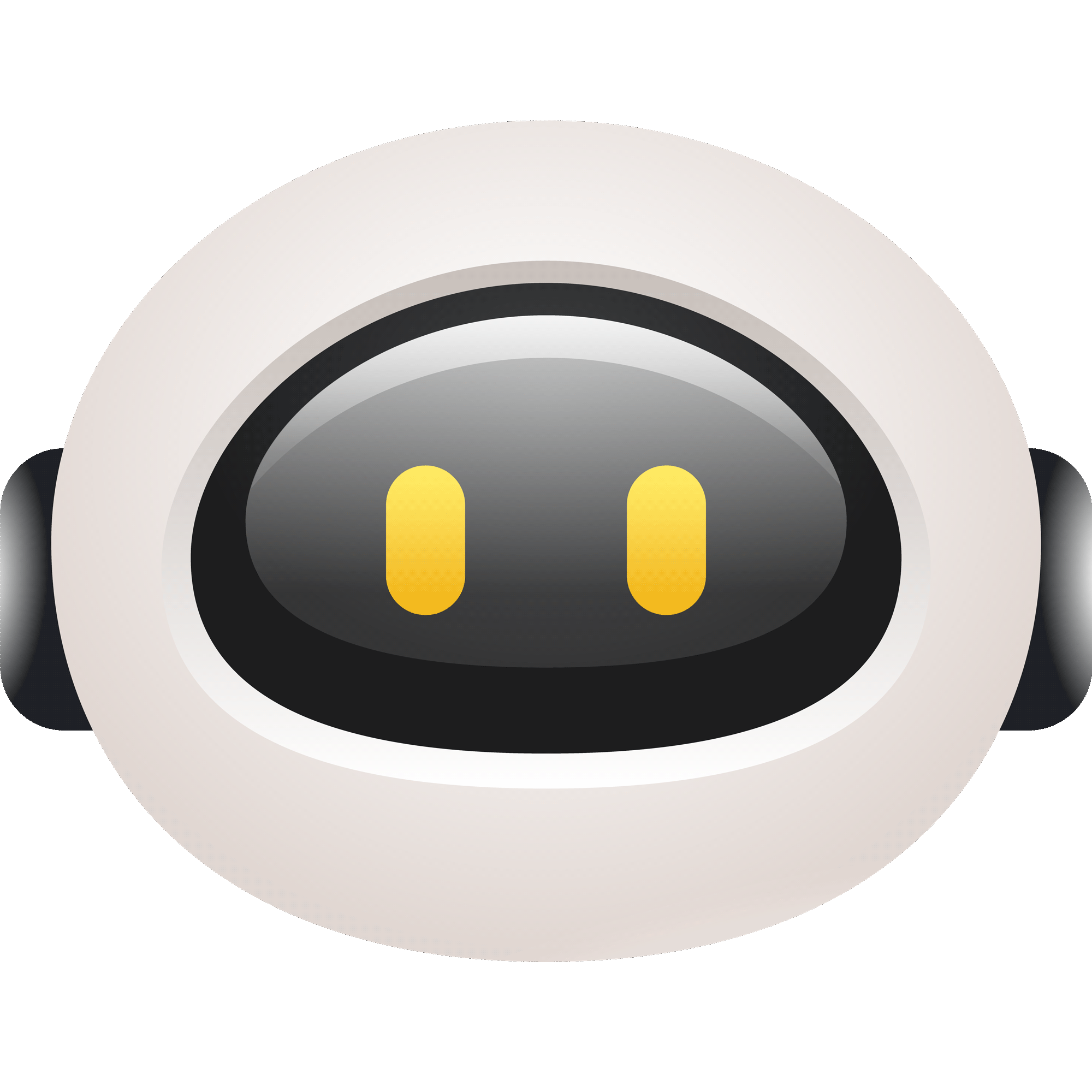


 iOS版下载
iOS版下载
 安卓版下载
安卓版下载